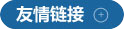这是我们讲述的第1113位真人的故事
我是张老酥
@两岸同舟
,1986年出生在台中,现在大陆生活。
2008年,我第一次踏上大陆。因为从小在台湾长大,对大陆都不太了解,直到那年
来到大陆后,见识多了才醒悟,原来自己的祖国是这么的强大。
我们家是中医世家,爷爷是第6代中医,在清代时期举家来到台湾省定居。一直以开药铺为生,生活还算稳定。
父亲祖籍广东,母亲祖籍福建,所以我们称自己为客家人。在台湾客家人的群体比较少,大约只有百分之十几。
家里只有我和妹妹两个孩子,在我上中学前家境还不错。父母亲在台中经营几家药铺,攒了一些家底。
展开剩余93%后来为了挣更多的钱,父亲又投资开了几间药厂。但由于没有办厂经验,投资失败,家道中落。
1999年的时候,家里本来还有一间工厂维持生计,可祸不单行,那年发生了9·21地震。那次地震是台湾南投20世纪末发生的最大的地震,震级为里氏7.6级。
父亲的工厂正好处于断层上,地震前后一直下很大的雨,造成厂房倒塌,中药材全部被雨淋。父亲组织工人进行了抢救,机器没啥事,可中药材全部不能要了。
这次地震对我们家来说不只是雪上加霜,更是灭顶之灾。
从那以后,父亲以及药铺的生意都是一蹶不振。因为有人上门讨债,家里经常吵架。没过多久,爸爸和妈妈就离婚了。
2001年我考上了当地高职的汽车修理专业,可读了1年,学费都成了问题。为了不给父母增加负担,高一结束我就选择辍学去打工。
因为高职学的是汽车修理,所以16岁的我进了当地一家汽修厂做学徒,包吃包住,每月工资1000多元。
每天的工作就是换轮胎、机油、搬电瓶、拆引擎等这些苦力活。
那一年,我和东南亚、印尼、泰国、菲律宾来台湾的打工者一起同吃同住,
日复一日地重复着一样的生活。我觉得这样下去没有出头之日,想改变自己的命运,必须读书。
于是在汽修厂干了一年,存了点钱之后,2003年我重新回到了之前的学校继续学业。
从那时起,我坚持白天上课,晚上去餐厅、便利店、铁板烧店打工。因为年龄小工作能力不足只能找到这样的工作,生活常常是捉襟见肘。即便如此,我也再没有和父母要过钱。
本来之前读高职是为了毕业之后赶紧找工作赚钱,为家里做贡献,可边读书边打工的经历,让我明白只有读书才能增长技能,才能活下去,知识改变命运是自己唯一的出路。
所以我决定继续求学,于是高职毕业我报考了远东技术学院的自动化专业。那时候想的是要掌握一门技术将来才能生存。
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为我打开了一扇窗,让我这个理工男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。
因为经常参与学校的各种社会活动,我对人文科学有了新的认识,也懂得了一个人不需要拘泥于自己所学的专业,可以多方面拓展。
我还是很幸运的,当时就读的远东技术学院,是一个专科学校,可到了2009年毕业的时候,学校升级为远东科技大学,毕业证升级为大学文凭,这为以后读研奠定了基础,也成为我去北大读博的敲门砖。
大学时期,我看了很多关于资本的书籍,就对整个社会的事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2008年亲眼目睹金融危机对台湾的影响,很多工厂停工,工人失业。我熟悉的自动化专业优秀的工程师也被工厂遣散,台湾百姓的生活陷入到了水深火热之中。
火车站、汽车站、地铁站到处都是露宿街头的人。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资本对人的影响,台湾的发展停滞了。可我从多方面渠道了解到,大陆却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。
那时候两岸关系比较和谐,台湾同胞可以去大陆探亲访友,我也很想走出台湾,去大陆看看。
当时我正读大三,并且在学生会工作,还担任系会长。2008年的时候,作为优秀学生代表,我有幸被选入大陆的参访团,这一次为我打开了了解大陆的一扇门。
出发前,同学朋友来送我,给我凑钱,让我买吃的喝的,不要饿着。在他们有限的认知里,大陆还停留在贫穷落后的阶段,我此去要做好吃苦的准备。
就这样,在2008年奥运前夕,我带着朋友们对追寻社会主义理想的所有寄托,以及我自己求索的使命,登上了前往大陆的航班。
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人生前景即将实现的那种兴奋还有紧张,以及伴随飞机起飞离心力的乱流所产生的不安。
第一次踏上祖国的土地,是从澳门拱北口岸到达广州。
我记得当时广州塔正在建设当中,我们参观了中山纪念堂、农民运动讲习所,还参观了烈士陵园、黄埔军校……之后又去了河南历史博物馆,最后来到首都北京。
在北京,我们参观了故宫、中山公园、人民大会堂、天安门广场和刚刚落成的鸟巢。
看着大陆到处都是雄伟的建筑,宽阔的马路,我的内心非常震撼,原本对大陆的憧憬变得更加深刻。
我相信自己找到了一条正确的,值得追寻的道路,因为我在大陆老百姓的眼里,看到了对美好未来的期望和愿景。
这次大陆访谈一共14天。从广东、河南、北京,然后又回到台湾。大陆之行让我不仅了解了真实的历史,也看到了很多新鲜的事物。
因为台北的城市很小,没有大规模的城镇,东西南北一个小时就可以走完。到了北京我才知道,原来中国有这么大的城市,这么多宏伟建筑,开车2个小时都走不出一个市,这对我是极大的震撼。
而且大陆是一个多元化的氛围,不同的城市有自己的方言和习惯,但整个社会是兼容的,和谐共存。
当我回到台北之后,把自己亲眼看到的大陆向同学和朋友们描述,他们都既惊讶又很疑惑,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,为什么他们的认知是错的。
这次大陆之行,让我对之前的人生规划有了新的思考。我是谁?我从哪里来?要到哪里去?
为了探索更多未知的领域,2009年大学毕业我选择了继续求学。
因为我想了解自己国家更多的历史,研究两岸文化,所以跨领域选择了金门大学国际事物专业,主攻大陆研究。就这样,我从一个理工男转变成了文科男。
选择金门大学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,因为它不仅有着特殊的地理位置,在学术交流方面和厦门大学非常密切,在那里可以接触到更多大陆的信息,我想通过这样的方式,更好地了解大陆。
从金门大学回台湾要坐30分钟的飞机,可去厦门坐船只要30分钟,这样的便利条件正是我所期望的。
研究生阶段我经常和同学坐船去厦门玩,认识了很多大陆朋友。在学术方面我也正式进入两岸关系研究的圈子,可以更专业、更准确地描述两岸关系。
2012年服兵役前后,我有了很多的社会历练和经验。但有些问题在台湾找不到答案,因为我想追求更高、更广的知识面。
那时候,我的目标已经很清晰,所以我来到了北大的台湾研究院深造。因为我的理论基础扎实,实践经验丰富,面试、笔试都很顺利,2013年我来到了北大读博。
进到这个顶尖的学府,接触到了更多优秀的人,在这里有人思考,通过知识来解决社会问题,做到了知行合一。一路走来,无疑我是幸运的。
在北大读书的时候,我一直想去西部支教。因为2008年来中国的时候认识了一些大学生朋友,从他们那了解到大学生会去偏远的地方支教,我看过他们拍摄的照片,也帮他们写过卡片。那时候就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。
于是,来到北大读书后,我通过各种渠道打听支教的流程。据我所知,在我之前,没有台湾学生参加过内地的西部计划支教工作。
在申请的过程中,我发现它的要求不低,而且非常有趣。因为自己的身份特殊,我陆续写了7万字的材料和报告来说明自己的身份和目的。
后来通过老师协调,一年多以后,我的支教申请才批了下来。后来我的行为被记录在台胞工作报告中——鼓励台胞参与支教工作。这让我非常欣慰。
当时大家都很好奇,我为什么要去西部支教?为什么要这么做?其实并不复杂,因为
我的初心就是希望和我认识的大陆青年一样,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点贡献,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
北大有自己帮扶的省份和地区。2014年我们支教团队从北京出发,一路运送帮扶物资先到达河北阜平,然后又去了云南、西藏、新疆、青海,每一个地方逗留10天左右。
最后到达了我的支教地——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大阪市。在那里我渡过了1年快乐的时光,也感受了大陆百姓的纯朴和善良。
直到今天,工作累的时候我还会去那里待上几天。
内蒙支教团一共派了4个老师,我们先在呼市培训了一个星期,然后去的赤峰。
我记得当时教的是初一5个班的地理,初二5个班的历史。学生平时都是住宿,老师不仅要代课,管理行政事物,还要照顾学生的生活起居。
支教期间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,让我久久难忘。
因为是一边读博一边支教,所以去内蒙的时候我带了很多书籍。记得有一天带学生跑完操,我把书放到宿舍门口,然后去做别的事。等我再回来的时候,我发现书没有了,然后就去找校长。
校长经过调查,发现是学校帮工的阿姨以为是没用的,拿去烧火了。当我跑到厨房的时候,书已经烧了一半,我只抢回了一半。
当时我哭笑不得,后来就想明白了,在城市觉得书是很重要的,可是对农民来说,有些人还没认识到知识的力量。
办公室里都是女老师,因为我的台湾普通话让她们觉得很温柔,经常会窃窃私语。她们说这个张老师讲话很娘娘腔,我听到以后就赶紧开始学内蒙话。
后来有次学生打架,我很严厉地训斥了他们,那些女老师才看出我也会比较凶,又说:“哦,原来张老师不是娘娘腔”。文化的差异让我觉得非常有趣。
学校有4个校长,有一个副校长专门分管学校后面的大棚。春天的时候有村民来帮着种菜,到了夏天,老师还要带着高年级的学生去采摘回来吃。
秋天的时候,老师要带着学生一起收菜,有一个帮厨的大爷会切几十缸的白菜和芋头腌制,够学生们吃半年。
春天带学生种地,夏天带学生采摘,秋天带学生腌制几十缸咸菜,冬天零下30度,值周的时候,还要早上6点起床带学生在操场跑步……支教生活过得非常有意义而且充实。
在物资运送考察和支教的过程中,我跟当地的老百姓进行了深入地交流,还帮牧民刷过墙。
我记得当时内蒙农村有一项十个全覆盖的工作,就是到最基层的嘎查村去帮助农牧民精准扶贫,我参与了当时的建卡工作。
虽然对于整个国家而言,这些都是很小的事情,但是我曾经参与了一线的努力奋斗,从城市到乡村,从内地到边疆,我认识到在这一片土地上有非常多的可为之事。这些事情对于我的人生成长有很大的帮助。
在北大读书期间还发生过一件有趣的事。当时有一个学弟叫林彦辰,他的爷爷在台湾呆过。我就和他说有没有机会可以一起去他的祖籍地看一看,就这样揭开了半张弦谱的故事。
后来通过我们认识的媒体朋友,对这件事情进行了内容挖掘,最后形成一首脍炙人口的,台湾同胞回到祖籍寻找到亲人的流行歌曲——《同唱一首歌》。
这首歌在台湾青年中被广泛的传唱。其实我们能看到台湾同胞的祖先,不论本省外省,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于大陆,就算是台湾的山地原住民和平地原住民,他们也是古越移民,也是来自于大陆。
年轻人寻找祖籍的回乡谒祖,接续族谱,其实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我是谁?我从哪里来?我要去哪里?这些疑惑都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答案。
因为支教和参加社会活动带给我很多感慨,2016年北大毕业之后,我更加注重实践。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关于两岸文化的介绍,之后在北京的培训学校讲课,从事的基本都是媒体相关行业。
多年从事媒体工作,让我喜欢上了这个行业。我从理工科直接跳跃到国际事物,这种跨领域的研究,既拓宽了知识面,也让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所在。
现在我每年都会从台湾带年轻人来大陆参观学习,或者短期生活,让他们自己慢慢地了解大陆,然后再创业或者找工作。
我给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,让他们更好地适应大陆环境,这是我这些年一直在做的事。
2017年我自己也开始创业,都是和媒体相关的,目前发展了3个板块,公益、自媒体、智库。并且在2019年我受邀到华侨大学博士后岗位执教。
在过去的9年间,作为两岸关系的使者,我一直往来于大陆和台湾之间,参与了两岸很多的重要活动。因为在台湾出生成长,在大陆求学立业,我认为我是有发言权的。
马上就要40岁了,精彩的人生该告一段落了。下一步我准备减少社会活动,专心在学术领域的研究,拿一些成果出来。再静下心来梳理一下自己的人生,写几本书。
也希望能有更多的有志之士参与进来,做一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。
人只有献身于社会,才能找到短暂而又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。
【口述:张老酥】
【编辑:目成】
我们不能走过不同的人生,却能在这里感受别人真实的故事,而且,每个故事都有真实照片噢!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真实的故事,请关注我们吧!
@真实人物采访
发布于:天津市